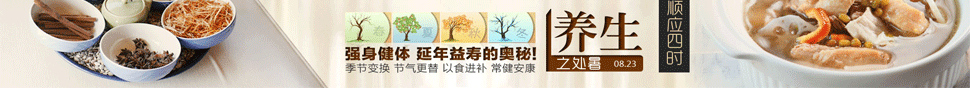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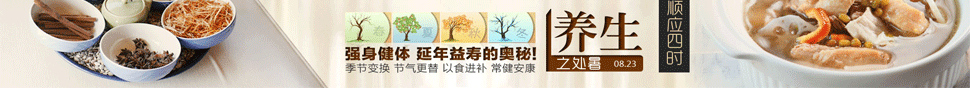
九月卅日
Friday,SEPT30,
年9月30日·星期五
农历丙申年·八月三十
“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是为华夏。”中国又称“华夏”,这一名称的由来与服饰有关。中国素有“衣冠上国、礼仪之邦”之美誉,而衣冠便成了文明的代名词,更是华夏礼仪的一部分。《尚书正义》注:“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由此而得名。
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始,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无数精美绝伦的服饰,中国的传统服饰文化在世界服饰的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中国传统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而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东方美学思想,依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审美风尚。
自周代开始,中国的冠服制度已趋于完善,孔子云:“服周之冕”,冕服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最高级别的礼服名称。主要由冕冠、玄衣、纁裳、白罗大带、黄蔽膝、素纱中单、赤舄等构成。冕冠是帝王臣僚参加祭祀典礼时最贵重的礼冠,“冠冕堂皇”的成语由此而来。凡戴冕冠者,都要穿着相应的玄衣和纁裳。玄衣即黑色上衣,纁裳即绛色围裳,上衣纹样一般用绘,下裳纹样则用绣。所用的纹样视级别高低有所不同,以十二章为贵。十二章为:日、月、星辰、群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山,取其稳重;龙,取其应变;华虫,取其文丽;宗彝,取其忠孝;藻,取其洁净;火,取其光明;粉米,取其滋养;黼,取其决断;黻,取其明辩。
十二章纹
古人素来敬畏天地与自然。他们将上衣分裁四片,即为了意喻“四季”;下裳分裁十二片,则为了对应“十二月”。其中袖圆以应“天圆”,衣领交叠成矩形以应“地方”,以寓“天圆地方”。古人将天地藏于衣服,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做人不可任性妄为,上有天,下有地,做人也要有规矩。
中国服饰的千年之美,华服背后更是一个古老文化的生生不息。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趣和思想内涵。如今,汉服很流行,很多人认为汉服指的是汉代服饰,其实不然,汉服是汉族传统服饰的简称。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这是出自汉代乐府诗《陌上桑》,诗中提到的“上襦”和“下裙”,指的正是罗敷身穿的服饰。“襦”是一种短上衣,一般长不过膝,衣领采用的是汉代常见的交领,并嵌有黑边,袖口宽大并且镶白边;而“裙”指的是一种束腰长裙。这种上衣下裙搭配组合的衣着样式,在中国古代女性最为常见,人们将它们合称为:襦裙。
明·佚名千秋绝艳图
汉代时的襦裙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有的甚至下垂至地,将长裙围绕在上襦外围,以丝绸做的腰带束腰,呈现出一种上窄下宽的视觉感受,给人以一种沉稳雍容之感。汉代乐府诗《羽林郎》:“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襦”,生动描写出长裙搭配丝带,而宽大的袖口与长裙相衬的华美,展现女子的飘逸灵动之感。
在汉代的服饰中,还有一种十分重要的样式:深衣,如果说襦裙展现的是女子清丽灵动,那么深衣则衬托出女性的华贵与大气之美。深衣是一种长衫,把上衣、下裳连在一起包住身子,使身体深藏不露,因而得名。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际,流行于先秦,男女通用,是衣裳分裁后再相连,下裳共用六幅,每幅又二分,以合每年十二个月。领式一般交领右衽,小口大袖,领和袖口通常为宽缘,腰间系丝织物大带,有曲裾和直裾两种。在汉代,深衣已成为女性的礼服。
在《诗经·扬之水》中有这样的一段诗:“扬之水,白石凿凿。素衣朱襮,从子于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诗中提到的“素衣朱襮”就是深衣了。传统深衣有三大讲究:一为“交领右衽”,衣服前襟左右相交,汉服为向右掩。二为“褒衣宽袖”,汉服的衣服都宽松,且袖子宽大,长过手臂。三为“系带隐扣”,汉服的衣服大多不用扣子,而用绳带系结。因而古人在身着汉服时,走起路来自然会潇洒飘逸,轻挥衣袖,便带起一阵清风。而现在的长衫、旗袍、连衣裙或是日本的和服,也都有深衣的气韵。汉代的服饰华丽多姿,清丽秀雅的襦裙,高贵典雅的深衣,为我们呈现出汉代女性独有的时代美感。
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卷
魏晋时期讲究风度气韵,褒衣博带成为流行风尚,《洛神赋图卷》中,身着褒衣博带式服装的男女比比皆是:曹植穿着当时士人的典型服饰,宽松的直领长袍,衣袖宽大,外衣里面穿着素色的单衣,下身系着宽大的长裙子;而画卷中女式的褒衣博带则是上衣宽松长大,外面套着半袖,腰间束着宽带子,下穿长裙,衣袖宽松,衣袖与裙裾随风飘逸间流露着耐人寻味的曼妙风韵。为了体现这种清逸的美感,此时的衣服都很轻薄,出于御寒的考虑,便出现了“帔子”,出门时披在肩上用来遮风暖背。随后爱美的古人发现,帔子随风飞舞时飘飘欲仙,很是动人,索性就把它加长变薄,这便演变成了敦煌壁画里飞天肩上充满着流动美的帔帛了,今天的披肩,也是从帔子变化而来。
唐朝的女子以丰腴为美,礼服多以合宜的袒胸、低领、大袖为主,走起路来大袖翩翩、华带飞舞,显得格外飘逸。也是因为身材微胖,唐代女子尤其喜着宽松的裙装,多为上身着襦下身着裙。襦要短且小,裙要肥且长。裙系高腰至胸部,甚至系在腋下,系扎丝带,颈部与胸部的肌肤露在外,给人以优雅、修长、飘逸之美。唐朝时期有种与襦裙相配穿搭的衣物也是深受男女喜爱的通性别服饰——半臂,对襟的款式,长到腰处,两袖宽大而平直,只到肘际。半臂最早出现于汉代,在魏晋南北朝时,因为礼教森严,故而衣着这种半袖衣的女人并不多,只是到了隋朝,数量才逐渐增添。
北宋·赵佶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
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
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
这首杜甫的《丽人行》,描写的是杨贵妃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情景,写尽了杨氏姐妹姿色之艳、体态之美、服饰之盛,尽显雍容华贵的奢华之风。
宋朝的时候理学思想盛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束缚下,人们抛弃了奢侈浮华的作风,那时流行“女子学恭俭超千古,风化宫娥只淡妆”,因此,宋代女性的服饰以简洁淡雅为主,多以纱罗绣绘图案或缀以珠玉。裙子中间的飘带上还常挂一个玉环,用来压住裙摆,使裙子不至于随风飘舞而失优雅之仪。这一时期的上襦衣领较高,披帛较长,遮挡功能较强,整体风格清丽灵动。清丽婉约的宋代女性服饰,一如那个时代流行的宋词,“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淡雅之美。
宋·苏汉臣妆靓仕女图
与宋朝相反,明朝是一个追求华丽的朝代。明朝的服饰,从衣料、色彩到纹饰无不一派艳丽之气。明朝中后期天气变得寒冷,为了保暖,明代的汉服上衣被拉长,露裙被缩短,衣领也从宋代的对襟领变为圆领为主。
到了清代,是中国服饰历史上继战国时代的“胡服骑射”、和唐朝“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满族人入关后,强制推行游牧民族服饰,以旗袍、马褂为代表。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明朝的冠冕、礼服。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代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
清·宫廷画师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屏烛下缝衣
清末的丝织、漂染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加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西结合,相容并蓄,清代服装崇尚繁缛华美,讲究丰赡细密的装饰效果,通常在领、袖、前襟、下摆、衩口、裤管等边缘处施绣镶滚花边,从款式、色彩到工艺都显示出清代对于服装细节装饰已达到巅峰的状态。清代由旗袍代表的繁饰美到汉装的袅娜美将古代中国的服装美学发展到极致,同时,中国汉族服装特有的“飘若游云,矫若惊龙”之神韵因对细节的过多索求也慢慢僵化、凝固,满族特色的旗袍影响至今。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自幼生活在江宁织造府,清代皇家专用的丝绸织造府,他得以耳濡目染,在服饰文化方面的审美和造诣精深,对于服饰织造的制作工艺、款式、搭配如数家珍,书中都有相关的体现。因此他笔下人物的服饰不仅丰富多彩、精美绝伦,让人从视觉上感受到美的冲击,同时每个人物的着装都与其自身地位及性格特征相契合,人物的服饰所用的色彩、材质、纹样、配饰等都不尽相同。
谭凤嬛十二钗之王熙凤
第三回里黛玉初至荣国府看到王熙凤:“这个人的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锻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曹公不惜笔墨,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凤姐的奢华着装,她的服饰色彩鲜艳、装饰繁多,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把一个精明能干、见机逢迎,妖艳凌人、魅力四射的王熙凤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其在贾府中显赫的地位和志得意满,同时她也一个贪欲极盛,且“机关算尽”入俗极深的人。
“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石青的衣服有五色刻丝,刻丝,又叫“缂丝”,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特色丝织工艺。在本色经丝上,将各色纬丝按花纹轮廓,一小块一小块用小梭子织成平纹花样。各色纬丝只在图案纹样需要时才与经丝交织,纬丝不贯穿全幅而经丝则通贯织物,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通经断纬”,号称“织中之圣”。这种“运丝如运笔,精巧疑鬼工”说的就是“刻丝”。古人形容缂丝“承空观之如雕缕之像”。缂丝成品的花纹,正反两面如一。织成物的图案和花纹,悬空背光观察,可见图案和花纹周边星星点点的洞孔,犹如镂刻而成。所以又被誉为“丝绸上的雕刻艺术”。刻丝完全是由手工织成,素有“一寸刻丝一寸金”之说。这件刻丝衣服,显示了王熙凤在贾府中的重要地位。神奇的缂丝工艺现在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缂丝团扇(嗜闲居团扇工作室)
第六十八回,王熙凤在接尤二姐时着的服饰风格却与她平时的风格截然不同:“尤二姐一看,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素如九秋之菊。”俗话说:“女要俏,一身孝”,她是以素雅的装扮包装出一种大家闺秀平易近人的姿态,同时以素雅的打扮与尤二姐暗中比美,这里显示了凤姐八面玲珑,工于心计的性格特点。
反观林黛玉,她是来自天上的绛珠草,自然是钟灵毓秀,不同流俗,从她旷世风华的服饰中也能窥见一二。第四十九回: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红香羊皮小靴”、“大红鹤氅”大面积红色的袖边襟下点缀白狐狸毛边,再加上那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鲜艳的红色服饰在素雪的映衬下,令她显得明艳鲜美、神采飞扬,飒飒如一树傲雪红梅,有种遗世独立的美,肃杀的雪地似乎都变得灵动起来了。
第八十九回宝玉去看她“但见黛玉身上穿著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上银鼠坎肩︰头上挽着随常云髻,簪上一枝赤金匾簪,别无花朵,腰下击着杨妃色绣花绵裙。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冉冉香莲带露开。”月白、杨妃色的色彩淡雅、清新自然,与她纯洁率真的性格一致,既不有意展示华丽,也不刻意追求朴素。
清·孙温《红楼梦》
曹公还采用了借喻名家之画的手法描写服饰之美,第五十回:忽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怪道少了两个人,她却在这里等着,也弄梅花去了。”贾母喜得忙笑道:“你们瞧,这雪坡上配上她的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在一个粉妆玉砌的冬天,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身后丫环抱着一瓶红梅,美人与红梅、白雪互相映衬,好一幅“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至美意境。
晴雯因为模样好针线好,贾母特意从自己屋里拨给宝玉。最能体现她女红技艺的是在第五十二回。贾母把一件金翠辉煌、碧彩闪灼的雀金裘赏给了宝玉,这件珍品是俄罗斯国的裁缝拿孔雀毛拈了线织成的。可惜只穿一下午,宝玉便把它烧了个指顶大的烧眼。因为裘衣太过珍贵,裁缝绣匠都不敢缝补。无奈之下,当时病重的晴雯只好强忍病痛熬夜织补:她先将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再将破口四边用金刀刮得散松松的,然后用针纫了两条,分出经纬,亦如界线之法,先界出底子,后依本衣之纹来回织补。这样的织补最需功力,不但要补全,更重要的是补好后,贾母等人看不到一丝破绽。好在晴雯手巧心细,她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体力不支,织补不上三五针,便伏在枕上歇一会。为保证万无一失,补好后,又用小牙刷慢慢剔出绒毛来。这样跟真的毫无二致。直到“自鸣钟敲四下”时才补完,这时晴雯也身不由己倒下了。雀金裘是补好了,也从此埋下了晴雯日后病中屈死的伏笔。
清·孙温《红楼梦》
《红楼梦》里几乎没有正面描写过晴雯的服饰,但通过她与服饰有关连的情节——撕扇作千金一笑、病补雀金裘、抄检大观园时提箱倾出全部衣物、临死前与宝玉换小袄,鲜明地突现了她位卑人不贱,刚义泼辣,爱憎分明的性格。正对应了“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寿夭多因毁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的判词。
《红楼梦》对人物的服饰描述可谓流光溢彩,熠熠生辉,各中的精彩数不胜数。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缩影,处处渗透了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服饰文化和审美,从服装到饰品,从质地到工艺,从款式到色彩,从着装到搭配,集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美之大成。
裳服礼仪璨华夏,一梦千年,再遇中国传统服饰之美韵,无论是罗衣飘飘的汉服,还是婀娜多姿的旗袍,每一种服饰之美都值得我们传承、完善和发展。
红楼梦日历
来自《红楼梦日历()》诗词版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shuanghuana.com/shpj/9399.html


